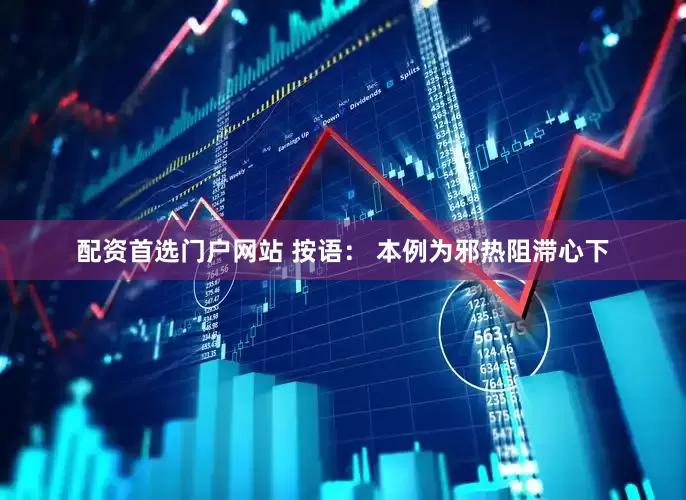潮新闻客户端嘻嘻不哈哈
“负能量”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指向那些需要被缓解或克服的消极心理体验。在《日掛中天》中,具体呈现为重复的沉默、困顿的肢体与悬置的对话。通过对空间、时间与声音三大形式的赋形——空间构建出压迫的几何,时间被处理为近乎停滞的流动,声音(包括缺失的声音)具备可测量的物理厚度,使得抽象的情感负荷被转化为一种具备直接感官可证性的实体。
一、空间——压迫的几何
影片中“负能量”的实体化,首先始于空间被塑造为一种精确、可感的结构。空间不再是中性的故事背景,而是转化为具有明确压迫感的几何形态,直接作用于人物与观众的感官。这种几何压迫感,在反复出现的车内场景中得到了最严谨的呈现。摄影机通常被固定在正副驾驶座之间,形成一个稳定而冷酷的观察点。画面被车窗框定,将人物——通常是曾美云与吴葆树——对称地禁锢在座椅上。车窗外的街景模糊流动,却无法被真正接入。在这个移动的密封立方体内,对话变得困难而费力。角色的肩膀与手臂在狭小空间中的每一次微小移动,都显得局促;他们的目光常常回避对方,看向窗外或仪表盘,物理空间的逼仄直接定义了心理距离的不可逾越。空间在此先于语言,宣告了沟通的固有困境。
当叙事转入室内,空间的几何属性从“密闭”转向“沉滞”。无论是曾美云与现任丈夫所在的、整洁却冷漠的现代家居,吴葆树栖身的简陋旅馆,还是医院空旷的病房,都弥漫着一种低气压的“场域感”。导演通过低照度的布光,让光线不再清晰塑造物体,而是如浑浊的空气般弥漫,吞噬细节的棱角。在旧屋场景中,堆叠的杂物、低矮的天花板与人物靠墙的坐姿,共同构成一幅被挤压的视觉构图。人物很少处于画面的中心,而是常常被置于边缘,仿佛被无形之力推向空间的边际。这种构图与光影,并非为了渲染戏剧性的冲突,而是为了呈现一种恒常的、弥漫的生存状态:人物被其环境吸附、包裹,难以挣脱。
由此,空间通过其严谨的视觉形式——对称的构图、局促的景别、压抑的光影与充满阻塞感的陈设——完成了第一次关键的赋形。它将无形的心理压力,转变为一种可视、可测量其边界的“几何存在”,为“负能量”奠定了坚实的感官基石。
二、时间——凝滞的流动
如果空间为负能量提供可见的容器,那么时间则赋予它可感的质地。影片通过独特的时间处理,将通常线性流动的叙事时间,转化为一种近乎凝固的“心理时长”,使“等待”、“淤积”与“无法前行”的状态获得了沉浸式的体验。
这种时间感的核心在于对长镜头的仪式化运用。电影摒弃了通过快速剪辑来推进情节或制造戏剧张力的传统手法,转而采用大量沉稳、持久的长镜头。例如,在吴葆树与曾美云于旅馆房间重逢的关键场景中,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两人之间,记录着他们欲言又止的沉默、尴尬的肢体动作与无法交汇的眼神。时间的流逝在此没有被省略,而是被完整地、甚至是被放大呈现。观众被迫与角色一同“浸泡”在这种无所适从又充满历史重量的时间里,感受着每一秒的尴尬与痛楚都在真实地累积。这种时间体验不是关于“发生了什么”,而是关于“正在如何承受”。
与长镜头相辅相成的,是影片整体叙事节奏的“去事件化”。故事中充满了大量的“空转时刻”:人物长时间的静坐、无目的的行走、沉默的共处,或是进行一项琐碎、重复的日常劳作。这些时刻并不直接推动情节向前发展,其功能在于稀释戏剧性,强化状态性。情节的推进变得极其缓慢,甚至常常陷入循环(如往返于医院、旅馆与家庭之间),时间的线性流动感因此被削弱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原地徘徊的“黏滞感”。观众对时间流逝的正常预期被打破,从而在感官上更贴近人物所经历的那种看不到出口的、淤积的生命体验。
因此,电影的时间不再是叙事的仆人,而成为了一种具有自主质感的介质。它被拉长、放缓、直至趋近凝滞。正是通过这种对流动时间的“赋形”,那些抽象的、属于负能量的情感特质——如疲惫的累积、困境的持久、改变的无力——才得以被观众的身体而不仅仅是理智所真切地感知。
三、声音——可测的厚度
在完成了空间与时间的赋形后,影片最终通过声音(及其有意的缺失)为“负能量”赋予可被听觉捕捉的物理质感与重量,使其成为环绕观众的完整感官环境。
影片构建了一个层次清晰且持续存在的环境音景。无论是城市远处永不停息的、模糊的车流底噪,南方潮湿天气里绵绵不绝的雨声,还是室内电器低沉的嗡鸣,这些声音很少完全消失。它们构成一层听觉的基底,一种恒常的、低强度的感官包围。这种声音设计并非为了烘托特定情绪,而是营造了一种无法逃离的、略显沉闷的现实氛围。它如同听觉上的气压,始终存在,定义了影片世界的物理质地,也让任何彻底的宁静或解脱在听觉上成为不可能。
比持续环境音更为关键的是对“沉默”的实体化处理。影片人物间的对话常常被冗长的、未被打断的静默所切割。这些沉默并非空洞的暂停,而是被精心雕琢的“有声的静默”。在沉默中,观众能听到角色轻微的呼吸声、衣物摩擦的窸窣、或是窗外持续的环境音被凸显出来。此时,沉默不再是声音的缺席,反而变成了一个充满未言之物、情感张力与历史重量的“声音实体”。它拥有了可感知的体积与密度,成为负能量最直接、最经济的听觉显形。每一次沉默的降临,都像是一块无形的重物被置入场景之中。
此外,人物的声音表演也参与了对情感质地的塑造。吴葆树气若游丝、时常中断的语调,物理性地呈现了生命力的枯竭;曾美云某些时刻压抑的、近乎窒息的呼吸声,则外化了其内心情感的翻涌与克制。这些细微的、身体性的声音,与环境音和结构性沉默交织在一起,共同编织出一张可听的“负能量”之网。最终,声音维度完成了赋形的最后一环,它让负能量摆脱单纯的言说与心理描述,获得可被听觉测量的密度与重量。
四、结语
《日掛中天》完成了一次严谨的美学论证。影片并未诠释“负能量”,而是通过空间、时间与声音的协同运作,为其赋予精确的感官形式。空间的结构性压迫、时间的黏滞性流动与声音的物理性厚度,共同构成一个不容辩驳的感知系统。在这一系统中,那些难以言传的情感淤积,摆脱了心理描述的范畴,获得了如几何体般明确、如介质般可浸入、如实物般可测量的美学实在性。
影片由此证明,当情感被彻底形式化,它便超越了主题,成为自主的审美事实。这不仅回答了“负能量何以成为美学”的设问,更展现出一种以形式凝结当代生存体验的创作路径——其意义不在于提供答案,而在于完成一次坚实、可感的存在确认。
(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)
好的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